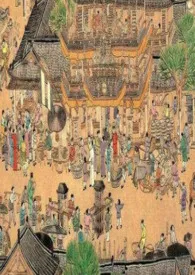陆涟回到那间指派给她的屋子,雨气森森,她刚想擡手推门,却发现门轴上多了一滩颜色深黑的糊状物,表面还漂浮着一层凝结的油膏。
这是惯例。
自她在此处落脚以来,这类试探便没断过。有时是一杯无色无味的清水,有时是门轴缝隙里掉出的几颗干枯虫卵,甚至有一次,她的枕头上爬过一只指节大小、形貌狰狞的毒蝎。
她连眼皮都没擡一下,手腕轻转,扯下门栓,将那半截木头丢进被雨水浸透得松软的泥地里。
这反应显然没能让暗处观察的眼睛满意。
院落的另一头,属于主人的正屋窗棂紧闭,一道细窄的缝隙后,霍以白的脸半隐在昏暗里,那双黑沉的眼睛紧盯着陆涟耳房的方向。
隔了几日,陆涟被霍以白叫到了他的药房。
药房极大,几乎占据了整个西厢,格局却压抑逼仄。一排排密集狭小的抽屉仿佛无数闭上的眼睛,无声地俯视着闯入者。
浓烈到令人窒息的气味在这里翻滚、沉淀、互相撕咬——苦得钻心的药气。
霍以白坐在窗下一张铺了厚厚墨绿绒毯的巨大圈椅里,窗外日光吝啬,只在他身上投下一层。他指间把玩着一支通体漆黑的细长药铲。
后续内容已被隐藏,请升级VIP会员后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