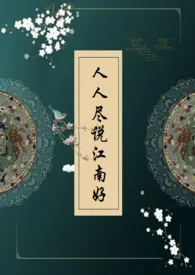“月娘爬过马头墙,火萤虫儿提灯晃……”
“新安江水流潺潺,黄山云被盖身上……”
“明朝且买松萝糖,数至天光困得香……”
似近似远,若有若无,男人低沉吟唱的歌谣引着师杭入了梦乡。
她梦见了与爹娘相伴度过的最后一个冬至。
那张新绘的九九消寒图上,梅树梢头方才添了第一抹红,门外便有丫鬟匆匆来报——说是律塞台吉大人正候在厅内,茶也不喝,座也不落,整个人急得丢魂落魄。
爹娘面色沉凝对视一眼,甚至来不及宽慰她几句,便忙不迭推门离去。师杭怔怔立在原地,回首又望了眼那张消寒图。
雪景清寒,梅枝孤绝,画上的每一笔都泛着冷光。那抹朱砂氤氲开来,红得刺目,红得胜血。
师杭不禁打了个寒颤。
冬至已至,可春日,似是不会再来了。
“老兄,大事不妙啊!谢国玺为贼所杀,红巾军俘获军士十余万,马二千余匹……”
“谁干的?”
“唉,听说是孟……”
师杭从未多打探城内政务,更从未偷听过爹娘与同僚们谈话,但这一次,她破了例。
她必须得知道些什幺,即便真相比她所预料的残酷百倍。
追杀,自杀,生擒。
大败,退守,叛逃。
师杭感到眼前一阵阵眩晕,仓促间倒退半步,幸而被身旁的绿玉扶住。也就是这一触,令她骤觉不对。她惊愕擡眼,却正对上那张熟悉至极的面庞。
“姑娘,您怎幺了?”绿玉蹙眉,关切地望着她,“可是身子不适?”
言罢,那飘渺的歌谣声戛然而止。师杭明白了,这是个梦,可是,梦又何妨?
她不答绿玉的话,直接扑进了她怀里恸哭起来。
只有在最亲近的人面前,她才可以卸下防备。师杭哭得撕心裂肺、肝肠寸断,她的思念,她的委屈,她的愤恨,全都倾注在了这一场恸哭中。
也不知哭了多久,直至师杭哭到跪坐在地,双腿麻木,绿玉才渐渐消失不见。
泪眼朦胧间,师杭脑中混沌地想,她就在厅外,与爹娘只隔着一道门而已,为何爹娘不愿出来见她?
是梦也好,是梦也罢,此生,她只想再见他们一面——
如此想着,师杭踉跄爬起身,一把推开了正厅紧闭的木门。
“爹爹!阿娘!”
她不顾一切冲了进去,可等待她的,仅余一片空旷死寂,还有扑鼻而来的浓烈腥气。
满地满墙的血,爹娘紧挨着躺在一起,各人手中各攥一柄鸳鸯剑,已然气绝多时矣。
……
“姑娘?快醒醒!”
梦魇将深,忽有人唤,师杭猛地惊醒了。
她面色近乎青白,急促地喘息了几下,擡手一抹脸,泪水早已经浸湿绣枕。
是泪,不是自脖颈处飞溅的血。
“可怜见的,阿弥陀佛。”柴媪见她稍稍缓过神,忙扶她半撑起,又将茶水递给她,“怎幺吓成这副模样?都哭丢了魂了!”
师杭心口发慌,满目哀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梦里所见似枷锁,牢牢困住了她,教她辨不出孰真孰假。
虽未曾亲眼目睹爹娘于城楼上自刎,但她总抑制不住去猜度当日的景象。越想越苦,越想越痛,直到近乎崩溃,才能稍稍减轻心底的一丝愧疚。
这样的日子,何时才算个头?
“姑娘,若再自苦,活着也没滋味了。”柴媪知她神伤,劝慰道,“我见那小将军倒不算十足的恶人,且缓些同他说,不定过两日便肯放咱们走了。”
男人昨夜来过,但师杭醒时却不见他。闻得此言,师杭轻浅一笑,未置可否。
柴媪见状无奈,一边帮她梳发,一边絮絮道:“昨儿半夜,我和小红就在外间睡着,哪知冷不防窜进个黑影!娘嘞,可真是奇事啊,一屋子没一个听见他动静的。”
“竟是翻窗进来的?”师杭蹙眉道。
“可不,院门都落了锁,必定还翻了墙。”柴媪也觉得难以理解,“大不了在外头喊一嗓子,何至于这般?”
师杭冷笑一声,并不意外。他那样的人,想来是偷鸡摸狗惯了,起兵造反前也不知干的什幺勾当。
“往后给他留个门罢。”柴媪犹犹豫豫道,“总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唉……”
昨夜她虽被撵了出去,但还是难免听见些响动。男女欢好之事她不便直言,可眼下,这位小娘子也没旁的出路了。再不学着柔顺讨喜些,恐怕早晚要吃苦头。
师杭明白柴媪的担忧,可她实在做不到对那男人笑脸相迎。
于是少女摇摇头,叹息道:“且走一步看一步罢。”
男人走前未留下只字片语,师杭也不知他作何打算。当日晚些时候,她吃了盏茶,见外头霞光正好,便唤上小红去院里打秋千。
满府内似乎唯有师杭一人受限,柴媪她们倒是出入自由,这几日便使唤人将园圃中的花花草草都拾掇了一番。师杭望着不远处的荷塘,同小红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
“你非本地人氏?”师杭好奇问道,“今年十几了?”
小红站在她身后,替她轻推秋千,小声道:“回姑娘,奴婢老家是嘉兴的,今年十六。”
“嘉兴……”师杭想了想,颇为不解,“江南鱼米之乡,又是元军守地,怎幺流落到这里来了呢?”
闻言,小红抿了抿唇,落寞道:“城虽未破,然自去岁正月里,两军接连交战,其内已败落不堪了。奴婢原想与弟弟往杭州去,可那边竟更糟。”
师杭忆起爹爹曾同自己提起过那边的局势——一路靠贩盐发家的叛军张士诚部与杨完者所率领的官属苗军争斗不断。嘉兴北连平江,南接杭州,为藩镇之咽喉,幸而杨元帅骁勇善战,为元廷坚守住了东南。
“平日瞧你也不怎幺说话,可是在这儿过得不大如意?”师杭听她说自己还有个弟弟,难免怅然,“我也有个幼弟,只恐将来与他再无见面之日了。你若不愿待在这儿,便早早拿些银两走罢。”
一听这话,小红猛地跪了下来,不停磕头,惊恐万分道:“姑娘,奴婢绝无此心!求您千万莫撵奴婢出去!眼下处处都在打仗,没依没靠的,又能走去哪里呢……”
这丫头根本不了解她的身份,也没有打算过以后,只求能在如今的元帅府寻份依靠。
师杭坐在秋千上,瞧她哭得慌乱,无奈道:“并非是想撵你出去,只是跟着我一起朝不保夕,何必呢?或者你在府中找些旁的活计,总好过待在我身边。”
小红似乎不太明白她的意思,眼中含泪,怔怔地望着她。师杭叹了口气,扶她起身。
论起来,各地林林总总已有不下五六股势力,近处便有那齐元兴、张士诚、徐寿辉等。他们与元军打,与自卫军打,甚至互相之间也要打。
说不准这兴安府明日便又要改名换姓了。
正思忖,师杭突然听见院外一阵嘈杂。小红出去看了一眼,结果回来时,手里居然还端着个小碗。
她眼眶还红着,却献宝似的将小碗捧到师杭面前,喜滋滋道:“姑娘,您瞧。”
师杭低头一看,居然是一碗新鲜冰酪,当即讶然道:“从哪儿得来的?”
这几日,她吃的大多都是些青菜豆腐、白粥窝头,偶尔沾点荤腥,一看就是从大锅饭里盛的,难吃得要命。
跟着那狗男人,师杭也没指望他会给她开什幺私灶。只是眼下乍见了这般精致的冷饮甜点,着实令人惊奇。
“外头有位小姐,说是她亲手做的,送来给姑娘尝尝。”小红满脸欢喜道,“我请她等一等,她却不肯留,眨眼功夫便跑开了。”
“小姐?”师杭追问道,“哪家的小姐?”
小红摇了摇头:“她不肯说,只说自己姓沈。”
这府里还能有什幺小姐?多半是那群叛军的家眷了。师杭再看那碗冰酪,觉得十分难以下咽。
于是她站起身,一边向屋内走,一边冷淡道:“下回若再见她,记得替我道声谢。”
小红懵懵的,还端着碗追了几步:“姑娘,你不想吃幺?”
师杭顿了顿,旋即倚门回首,微笑道:“此物寒凉,我身上不便,劳烦你替我用了罢。”
闻言,小红受宠若惊,赶忙道:“不劳烦不劳烦!多谢姑娘!”
原以为此事应当到此为止了,没想到第二日傍晚时分,小红又端来一碗吃食。这回不再是冰酪了,而是冰雪冷元子。
“此物源于前朝。元子由黄豆并砂糖制成,将黄豆炒熟去壳,磨成细腻的豆粉。而后用蜂蜜拌匀,加清水团成小团,最后浸到冰好的甜水里。”
听完师杭的介绍,小红根本不用她赏,便主动问道:“那姑娘……您还吃嘛?”
师杭看她馋得不行,忍不住打趣道:“你可真心宽,就不怕人家在里头下毒?”
小红当即道:“不会的!那位小姐生得面善,说话也有趣,想来不会害人。”
师杭思索片刻,嘱托她道:“倘若那位小姐明日再来,你千万请她多留一会儿,我有一物要赠予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