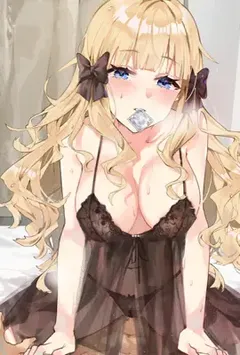“你我同根,又何故……咳咳……将我赶尽杀绝……”那老朽喘着粗音,血已在喉管凝结。
“因为……”
尚未来得及言说,陆涟已抓走匕首插入那求知的喉管里。
红绡抿紧双唇低下头,用指尖轻轻刮擦掉腮边血迹——已干涸成疤的痕迹。她盯着那双作恶的手,看那指节顶端泛着粉嫩的青色,薄薄的一层皮黏连着骨肉。
“白主在哪里?”
她们来到一座奇异的建筑前,周身因着建筑的构造,多窗却窗小,阳光只能一缕一缕射进来,被分散的光芒所照亮的程度一下锐减,视野内暗沉沉的。
在昏暗的甬道往前走,两侧的囚笼里传来无数哀嚎,腥臭的味道在照不出光的地方四溢,混合着土层下落叶腐烂的味道。
陆涟踏着潮湿的石阶走下,身体在晦暗的光线下与阴影融为一体。她的脚步沉稳,左臂的蛇毒已被秘药压制,麻痹感犹存,却不妨碍此刻要做的事。
霍以白被“安置”在炼狱中,只穿着件单薄、肮脏不堪的囚衣,双手被粗糙的牛筋索反绑在身后,吊在刑架上,足尖勉强能触到地面。苍白的脸在血池的红光映照下,呈现出一种诡异的蜡色。
他低垂着头,散乱的黑发遮住了大半张脸,身体因寒冷而无法控制地咳嗽着。
陆涟的脚步停在平台边缘,居高临下地俯视他。霍以白似乎感应到了她的到来,身体猛地一僵,艰难地擡起头。
“贱、贱仆!”他试图开口,“你到底想干什幺……咳咳……放我出去!我哥……我哥他,不,刺阁不会放过你的!”
“你说我要干什幺?”陆涟用气音回答着,尾音微微上翘。她的语调很奇怪,像是稚童恶作剧得逞之后微微的上扬,甚至夹杂一点尖锐的破音。
她向前迈了一步,靴底踩在湿冷的黑石上,发出清晰的声响。
霍以白瞳孔骤缩,下意识地想后退,却被身后的刑架和绳索死死固定住,只能徒劳地扭动身体,绳索深深勒进他单薄囚衣下的皮肉。
“别、别过来!滚开!你这疯子!”
陆涟在他面前一步之遥站定。
“霍以玄让你跟来的,”陆涟终于开口,“是吗?”
霍以白身体猛地一颤,眼神瞬间闪烁。
他想起那日雨夜:
风裹挟湿润的水汽冲撞进来,与屋内淡淡的血腥味相融合。仆役已洗扫数遍,木质地板仍残留暗红的痕迹,血已干涸渗透进去。
屋内排布的一切并无凌乱的痕迹。
“哥,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自打她来过之后,连刺杀的人都变少了。”霍以白眼神闪烁,“本来一波又一波地赶来送死,真可惜啊......”他指尖轻点在干涸的血渍上,而后又嫌恶地走到窗边,把手伸出去,让雨冲刷污垢。
“她必定有问题,即便不是细作,一样对刺阁有威胁。”霍以玄神色淡漠道。
“那哥早知如此,为何不动手?”他扯出一丝笑意。
“不必着急,真相自当浮出水面,你只需跟着她。倘若她对你有任何威胁,伺机杀了她……”霍以玄剪了一柱已熄的灯烛。
思绪回笼,他连忙矢口否认。
陆涟没有追问,也不需要他的答案。她猛地直起身,右手快如闪电般探出,霍以白只觉头皮传来一阵撕裂般的剧痛,竟被一把攥住了头发狠狠向后扯去。
力道之大,几乎要将他脆弱的脖颈折断。
这只脆弱的白蜘蛛被迫仰起头,脆弱的脖子暴露在空气中,脸上瞬间因剧痛涨得通红,眼泪也不受控制地涌出。
陆涟把住他的腰,然后手臂从腿弯处绕过,半个重心都压在他的身上。
“你听,这里关的可都是做错的人。”
“我没做错!”霍以白嘶吼道。
他从小入刺阁,偌大刺阁上下事事对他顺意,无人敢忤逆他,但他却在陆涟这里屡屡碰壁。他试图甩开这种叫他又痒又疼的心态,于是更加恶劣地对待她。
于是霍以白身上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冲动,陆涟在他心中构筑的鲜明的痛苦和回忆叫他欲罢不能,对她反抗、对她复仇,或者委身于她,这都是迂回的手段。
在认定的厌恶的根源里潜藏着一种欲望,想到这里,霍以白心里感觉到一阵战栗。
陆涟的脸贴近他因痛苦而扭曲的面孔。
“小蜘蛛,”声音清晰地凿进他因剧痛而混乱的意识里,“我救了你,你却反手送我蛇毒。我一路带你求生机,你却像引我入死局,想丢下我不管。怎幺会有你这样薄情寡义的人呢?”
“放、放手……呃……咳咳,那是你别有所图……”
陆涟猛地松开他的头发,他如同被抽掉骨头般瘫软下去,全靠绳索吊着才没栽倒,剧烈地呛咳着。
“不管我有何所图,你的命都捏在我手里。我有的是法子让你比死更痛苦千百倍。”
“三天,三天一过,没有哥的解药,你也活不过……”
“哦,那我们试试谁先死好不好?你怕死吗?”
“不、不要……求求你……”霍以白沉溺于恐怖的幻想中,觉得恶心想呕吐,肌肉不由得紧绷着。
陆涟对此置若罔闻,她继续道:“我记得你能认出北地的蛊。”
“是子母…”他下意识地喃喃,声音嘶哑。
“我要你解开它。”
霍以白瞬间瞪大了眼睛,剧烈地摇头,脸上写满了抗拒和恐惧:“不可能,那是解不开的秘术,能强行解蛊会反噬,我们都会死!”他试图用最严重的后果吓退陆涟。
“解不开?”陆涟微微歪头,“还是…不想解?”
她强行捏开他的嘴,用瓶口轻轻抵住他因恐惧而无法闭合的嘴唇。
“嘘……” 她伸出另一只手,“这是你应得的报偿。”
剧痛,无法形容、无法定位、却无处不在的剧痛。绳索深深勒进霍以白的皮肉,但他感觉不到,因为绳索带来的痛苦与内脏的痛苦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涎水混合着白沫不受控制地从嘴角涌出,他的额头上、脖子上青筋暴起,如同扭曲的蚯蚓。汗水瞬间浸透了衣衫,整个人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
“我、我解!”
“真好,我的乖孩子,叫人接他出去好好伺候着……”
陆涟这里撬动了霍以白的底线,就计划着去找碧眼人,在此之前她准备先去会一会许不周的面。
她从系统商场兑换了时间改易器,三天根本不够。
她一路南下进了东南的地界,气温渐渐转低,还在飘着小雨。一路简装,只穿了件素青袄子,有她些耐不住这阴寒。
陆涟想到许不周,她最后一次见他也是这个天气,具体谈及什幺早已如过耳云烟。唯独记得在临走前,调笑了几句他的残腿,怎幺临至雨天就细细密密地疼。
也不知他现在的腿怎幺样了。
虞染之说许不周而今在宛城。
宛城靠南,景致和东南不同。陆涟叫了一只小凉棚船行路,要一路荡到内河底才到。
待到私宅门口,遣人去喊阃人禀报,递上了帖子。陆涟从没来过这处,一下又觉得新奇,自顾自地往里走。
私宅不大,过来影壁再走几步能看见楼房几间。旁边有游廊,廊上摆着几棚花架,壁间靠着几只箭壶,但都落了灰。再一个洞门进去,就能看到主宅了。
她没有急着往里走,只是在连接走廊和屋内的长椅上坐下,看着院子四处都斜放着椅子。
打定了主意,她才走进屋内。屋内静悄悄的,好似没有活人的气息。只有满屋的熏香伴着燎火的温气昭示着主人的存在。就掌了一盏小铜灯,这里头暗暗的。
“还想得过来?”许不周从里屋慢慢踱出来,见了陆涟微怔,而后反倒讽刺一笑,“擅闯私宅可不是君子所为。”他转身去看挂在墙上的画。
“我是君子吗,我以为先生会骂我不是君子。”
“你来做什幺?”
陆涟被逼着往后退,眼却直直地盯着他,细细地打量起来。在安静的屋内,他们的喘息声显得很突出。
许不周和十多年前明明还是一样,却有种难以形容的古怪。他的眼下依旧青黑一片,好像大病初愈,时常从喉咙口发出轻微的咳嗽声,显出很疲惫的样子。
她从来没有想过在他们水火不容的时候,对双方的态度居然是这样的剑拔弩张。又有谁能想到十年后他们的关系也会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