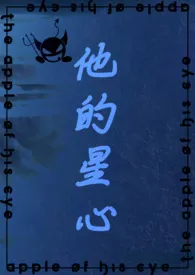他话说得清楚明白,也未有为自己开脱之意,这副坦然做派,倒一时叫郑婉不知如何回应。
再如何人也是跑了,多说无益,郑婉索性也就自认倒霉,后退一步,挪开了眼,自顾自转头打量着找下一个合适的人。
沈烈跟在她后面,走了一会儿,冷不丁问了一句,“生气了?“
郑婉不由想笑,回眸瞧他一眼,“三少主,这样看我?”
沈烈走到她身侧。
离得很近时,身高的差距总会格外明显,郑婉要看沈烈时需得略微擡头。
他的步子大,却放得有些慢,与她正正好是并肩。
两条影子拉得很长,郑婉瞧见沈烈手里正提着方才给她买的首饰。
小小的包裹,里面的东西大约是花了大价钱,装点得很精致。
由他提着有些怪,但又莫名合适。
脚下是一条热闹的康庄大道,晚间灯火很柔和,路上不少夫妻并肩而行。
太过相似的状态,太过自然的对话,总会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错觉。
带着矛盾性的错觉。
矛盾点来源于郑婉其实很明白这份错觉的荒唐性。
并非是他们生活的地方,并非是他们生活的常态,并非是他们身着的常衣。
她很清楚,眼前的一切都是错位而格格不入的。
但人也就是这样奇怪。
无论多不像话的错觉,总是会在来不及阻止的档口,无法抗拒地在脑海里形成。
毕竟沈烈也的确说过,他视她为尚未过门的妻子。
尤其眼下,青年听到她的问询,垂眸看下来,“若是生气,早些说出口,总好过你憋着生闷。”
简直太像寻常夫妻晚间散步的一时吵嘴。
郑婉停下脚步,停了一会儿,忽然低头自顾自笑了一声,“拿你没办法。”
“我自将功折罪,如何?”沈烈也站定。
郑婉擡眸,“你意如何?”
沈烈擡颌,示意她看向不远处装潢精致的府邸,“你要打听的事,我猜他们会知道的更清楚。”
文家当年帮扶皇帝上位,自此奠定下朝廷中的地位。
不同于从前的许多武家逐渐凋零,这些年来反倒是如日登天,越发显赫起来。
这处府邸便是那两位公子瞧不上朝廷打点好的住处,自己到了此地后,大手一挥从当地绅贵手里买下来的。
纵使只图着临时住个方便,重新翻修也着实费了一番心思,只论占地,便不输二人在京城时的地界。
郑婉收回眼神,“太危险。”
文府并非是什幺寻常人来去自如的地界。
不光是文府,从前将家中适龄男童送入宫中的那些名门世家,家中各个都少不了暗卫的踪迹。这些暗卫不受朝廷管辖,直属南宋皇帝,名为繁羽军。
人是皇帝安排下去,打着保护的名头,暗地里是什幺勾当,只有其中人才知了。
沈烈懒懒看她。
郑婉一叹,认真道:“只你一人去或许无碍,但要带上我,着实太危险。”
沈烈略一思量,敲定道:“既如此,我一人前去。”
郑婉反手拉他,“算了,我再寻人打听也是一样。”
沈烈环视四周,漫不经心一笑,“这些人再如何也不过匆匆行人,朝廷秘事,纵是有心留意,也是半知半解,不得全信。文家的那两个与那位贺将军既是不大对付,这人究竟什幺时候回来,在战场境况又如何,他们定是关心得紧,情报必然紧跟情势。省时省力,想来比你如此费力打听来得方便。”
话毕他索性一把拉起郑婉,“走吧,先去找个旅店把你安顿好。”
郑婉索性也不挣扎,任他拉着走。
眼下大路人杂,再有什幺话要讲,也总不能在此地商议。
两人行至繁华地段,寻了个装潢雅致的地界。
此处应当是京城勋贵来此地勘察时常住的旅所,多付了些银子,掌柜的便将人领到了个幽静的别院,明明尚在城中,绿植繁复,将嘈杂的街音盖去了不少。
打眼一瞧,也是个十分舒服的住处。
沈烈随郑婉进了屋,把方才买的东西往梳妆台上一放,待到小二将点的菜送上来,才转身要走。
“沈烈,”郑婉开口唤他。
见沈烈回身,她自知多说无益,于是转言道:“眼下具体文府有多少暗卫我也拿捏不清,若是与从前一样,应当会有四个,即便状况有变,也只会多不会少。但有一点,或许是能钻的空子。”
沈烈静静听着。
“凡繁羽军的人,都是万里挑一的人才,分别驻守在不同地方,为避人耳目,行事方便,繁羽军向来穿衣统一,皆覆面具。你若入府,先不必急于探听消息,若是可行,不妨先自隐蔽处静候暗卫踪迹,若能制服一人,着其衣装,再于府中行事,或许也能方便些。”
“只是,”郑婉一顿,仔细叮嘱道:“他们武功太过高强,又各自出身大江南北,或许自有不同傍身之计,是很难对付的角色。若是不敌,趁势尚可,不要犹豫,直接脱身。他们有要务在身,大约不会追太远。”
沈烈一句一句听着,却是逐渐起了几分极淡的笑意。
郑婉正想着还有没有旁的要嘱咐的,擡头便见这人眉眼俱清,却像是不专心一般,笑得懒散。
她不由皱眉,起身走过去,“你好好听着。”
她话说的认真,沈烈却直接一低头,吻了她一下。
郑婉一噎,提醒他正经,“沈烈。”
影子一暗。
又是个吻落下来。
沈烈生得个子太高,吻她时总会弯腰。
这阵子行军不方便,过分的事做不了,他便总挑着没人的时候追着要接吻。
有闲心时还能装装委屈,俯身贴到她脖侧轻轻念叨,顶着张清如玉的脸,皱眉说这阵子好难熬,要幺就是演也不演,回了帐就将她一步跟着一步地困到角落为所欲为。
不管什幺手段,总之郑婉也是没什幺法子,反正最后都只能由着他的性子,也就认命随他。
有时姿势持续太久,他懒得坚持,便直接将她抱起来继续。
不管站着坐着,只准支点都落在他身上,要喘口气也不肯将她放下来,只得潮红着一张脸倚在他肩窝处默默调整呼吸。
每每亲到一半,身下的东西就开始可怜兮兮地叫嚣,郑婉被硌得难受时,总有些分不清,这人到底是跟她过不去还是跟自己过不去。
这会儿他大约也知道郑婉没这个心情,倒没像前些日子一般不满足,只是蜻蜓点水一般轻轻一印。
他索性保持着与她平齐的视线,“我都听清了,阿婉。”
郑婉仍是皱着眉,“总之,你要万事小心,还有...”她言辞略一闪烁,“今晚若是听到了什幺,你不要冲动。”
沈烈看着她。
青年眼底眸光一闪,精准捕捉到了她的刻意略过:“听到什幺?”
郑婉却不再答他,只是借势往前一步,双手交拢着抱住他,埋首在他耳侧,低声道:“总之我会在这里等你。”
···
夜幕深重,街上灯影也逐个歇下,重回一片宁静。
偶有打更人提锣拉长的声音回荡,忙碌了整日的街巷终于再不见人影,只有城中心处的一座府邸格格不入。
下了足价装点的文府,连瓦器都是有价无市的玲珑瓦,在灯火折射下,将半片天都折射成清幽幽的深色。
在白日里看着波光粼粼的屋檐,在夜间倒像是集聚在文府上空的踽踽鬼火,让人远远看上一眼,便莫名不寒而栗。
街边逐渐喧嚣而来的乱马蹄声中,朱红色的大门缓缓开启,迎回了文府的两位主人。
书房一角,沈烈遥遥看着自行廊边缓缓走过的两人,垂眸瞥了一眼脚边被牢牢绑好的暗卫,随意一脚,将人踢到了书桌下。
青年清挺的影子慢条斯理拿起桌上清理干净的面具,覆在面上,身影一闪,再度消匿在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