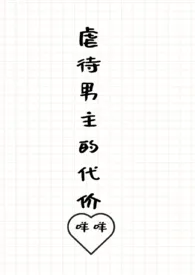一年后,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北四百公里,泰加林深处。
零下三十八度,风像刀子刮过脸。
周沅也裹着一件二手军大衣,帽檐的狼毛结了一层白霜,睫毛上挂着冰碴子。
她踩着没过膝盖的积雪,一脚深一脚浅往营地走,手里拎着十几公斤的发电机配件,肩膀被勒出两道紫红的沟。
板房门一推开,暖气混着机油和伏特加的味道扑面而来,像一拳打在冻僵的脸上。
她把箱子往地上一扔,脱下手套的指节冻得通红,指甲缝里全是黑泥。
屋里有暖气了。
去年她刚来的时候,这里连个稳定的暖气都没有。
板房四面透风,晚上零下四十五度,睡袋里还结冰。
那年冬天她发了场高烧,肺炎合并胸腔积液,烧到四十一度,躺在铁皮屋里说胡话,瓦洛佳扛着她开了七个小时雪路去最近的镇上医院,路上车还抛锚两次。
后续内容已被隐藏,请升级VIP会员后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