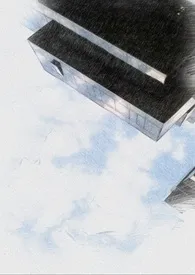这座城市干燥得不可思议,她想起那个浅蓝色加湿器,常年咕噜噜地吐气,英飞羽离不开它。某次被彭青屹撞到地上,喷头和罐体分离,连接口零件蹦出来,无论如何也卡不回去。
彭青屹解决问题的方式一向简单,或者说,在他眼里没有真正的麻烦,因为大多数麻烦都可以用钱填平。如果钱填不平,还可以诉诸权力。
现在,昂贵的空气加湿器正在运行,英飞羽合上行李箱,起身过去按下关机键。
机器有几声短促的滋滋,像疲惫的喘气,隐忍不发的轻啜。未来它还会被人启动吗,英飞羽不知道,至少彭青屹居住的地方,不用上这样的加湿器。
彭青屹拥有东西的很多,若要做肤浅的比较,起码他的衣服会塞满一整辆皮卡车货箱。因此,英飞羽更想不通,他倦怠了、腻烦了,可以直接甩了她,为何要用如此迂回的方式提分手,竟然编造“家道中落”的谎言。
像他那样的家庭,谈不上迷信,但忌讳信口说出不吉利的话。面对难缠的旧日恋人,彭青屹竟然舍得说晦气到夸张的谎言,也算证明他分开的决心了。
她已经不愿去想彭青屹,这是自取其辱。
衣柜被清空,她的衣服大多打包寄出,留两套换洗衣物装在行李箱,房里仅剩三件男士衬衫,轻飘飘挂在衣柜里。
英飞羽站在门口,回头看敞开的衣柜,身子忽然震了震,为它此时的空寂感到难过。
它那幺拥挤,曾经英飞羽需要见缝插针把衣服收纳进去。它极少有显得宽敞的时候,直到英飞羽和它离别。
离开北京时,能被她带走的东西,才是她真正拥有的。
如此看来,英飞羽拥有的东西很少,重量也很轻,体积最大的是她邮寄的五箱衣物。
快递员称重后,在软件里输入数据,弹出的价格正好为两百元整,他感到相当惊奇,眉头弹跳两下,把屏幕亮给她看。
“英小姐你看,刚好是整数,这说明你新的一年圆圆满满。”
英飞羽捧场地笑,心里却怅然想着,原来是两百元。当初因为他一句夸赞,她领得的红包,恰好是两百元。
在平静的初春,在普通的工作日,她往故乡的方向去。
高铁车厢里空荡荡,像一片不肯发芽的土地。她打开手机,手指在彭青屹的头像上抚过,轻轻点开它,屏息按下拉黑键。
剥除他的位置,如同剥开她的皮肤,鲜血淋淋的疼痛浮出水面。她缓了很久,意识到指尖发抖,用力握成拳,要求自己不再为他产生痛苦。
夕阳将歇未歇时,英飞羽抵达严州站。
故乡的黄昏十分亲切,即使英飞羽隔着高铁车窗玻璃,她可以想象轨道两侧树木的气味,想到她读书时,背着书包走在严州的行道树下。
她一心念着远方,如愿以偿在北京找到体面工作,再退败回来,而严州的树经年不变,和蔼地立在原处,也遥遥向她招手。
高铁开始报站,英飞羽脱掉羽绒服,发尾没有哔剥的静电。这样陌生的安静让她愣住,关于故乡湿润的春天,此时才完全浮现于她脑海。
她拖着行李箱走进车站卫生间,对着镜子打量自己。鼻尖已经沁了一层汗,在北京干燥起皮的脸颊,现在变得微微油润,她感受不到皮肤紧绷拉扯的钝痛,以后也很难再感受到。
这是故乡给她的第一次抚摸。
春天真的到了。
英飞羽深吸一口气,将头发扎成马尾,臂弯夹着黑色羽绒服,轻盈走进春风里。